【開放網按: 徐澤榮博士是深具中西文化素養的社會學者。2000年入冤獄11年,獄中筆耕不綴,苦研馬學,心得盈筪。自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州監獄遭遇了滑鐵盧!」作者改稱馬克思主義為馬學,而馬學之核心乃是勞動價值學說,本書即力證其說之非。以此見證馬學入中100年。系列共20章,本刊將予連載。】

復旦大學陳其人教授(左二)早年照片。人稱譽其「治學不為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後人」,
他對之曰「執教著文中有我,吃飯穿衣外無他」。
世事難料,所啟後人竟然有後於獄中將馬學勞動價值學說證非的我。
【馬學勞動價值學說邏輯證非系列之一:索品】
人類誕生之後通過勞動追求和通過市場交換的,並不只是產品,即人造效用,而且還有「索品」,即天設效用。產品源自生產勞動(Producing labour),索品出於「索要勞動」(Possessing abour)。人造效用無非是經過人力作用的天設效用的分解與合成,縮小與擴大、移動與固定、拆開與整裝、曝露與隱藏等等。陸水空天,樹草土石,禽獸魚貝,以及社會關係、生物關係、天–人關係、事–物關係等等,一經對其有所需求的人類的佔有,便可稱作天設效用,或者稱索要勞動的成果「索品」。一邊被提供一邊被消費的生產勞務和索要勞務,無法像產品、索品那樣收凝勞動時數——於此場合,勞動時數不被收凝,只被流淌,而以勞動時數為效用序數計算單位。產品、索品、生產勞務、索要勞務四者之間的交換形式,乃有以下十種:
01. 生產勞務與生產勞務之間的交換;
02. 索要勞務與索要勞務之間的交換;
03. 生產勞務與索要勞務之間的交換;
04. 產品與產品之間的交換;
05. 產品與索品之間的交換;
06. 產品與生產勞務之間的交換;
07. 產品與索要勞務之間的交換;
08. 索品與索品之間的交換;
09. 索品與生產勞務之間的交換;
10. 索品與索要勞務之間的交換。
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定義廣義經濟學為「關於各種不同制度形式下的所有交換活動的一門科學」;並稱「交換給交換雙方帶來好處的根源」為何,乃是經濟科學的核心問題。作者認為上述十點業已窮盡了「所有交換活動」的形式,儘管布氏如同其他經濟學家一樣,並沒談到索品及索要勞務。有些索要勞動本身,如搶劫、戰爭等並不必然帶給雙方好處,但是,索品、索要勞務的交易——例如劫贓與虜獲的交易,卻像產品、生產勞務的交易一樣,會給交易雙方帶來好處,至於好處是否長久、對等,則是另外一回事。不過,由於許多對於索品和索要勞動的獲取,牽涉到威權,牽涉到暴力,所以它們亦屬政治科學的研究物件,或屬「政治經濟耦合科學」的研究物件。
就像馬克思將勞動分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曾具振聾發聵作用一樣,本書將具體勞動分為生產勞動和索要勞動,更具振聾發聵作用。對於馬教教徒而言,後種分法還有可能使得他們聞後即現瞠目結舌,如果不是即感五雷轟頂的話。
「勞動」的經典定義,乃為「人類使用工具改變勞動對象,使之合適自己需要的有目的活動」。索要勞動的外延無疑符合這一內涵。宮殿、儀仗、鑼鼓、飾物、標語、武器、工事、界碑、禁柵、城牆、文字、書刊、儀器、電腦等等,都是索要勞動使用的工具。你不能說它們不是工具而是別的什麼器具——吳王宮女誤將武器當作玩具,便被得到吳王允許訓練她們的孫濱下令斬首。天設效用的「改變」可以包括:「生命的傳續」、「財寶的易主」、「技能的提升」、「西學的東漸」、「權力的旁落」、「爵位的剝奪」、「道德的淪喪」、「感情的轉移」等等。求知索解活動的鵠的乃是一種天設效用,即客觀規律的形而上式道化肉身——「知識」。客觀規律不能被人製造出來,所以不能將求知索解活動歸入生產勞動;奪取政權活動的鵠的亦是天設效用,人類具有「施治–受治」基因,蚯蚓、蝤蠐、蝴蝶、瓢蟲之類卻沒有,你亦不能將奪取政權活動歸入生產勞動;體育競賽的鵠的既有人造效用,如貨幣,亦有天設效用,如健康,不過體育訓練和運動競賽乃與生產勞動無涉。
索要勞動也像生產勞動一樣,分為作業勞動和經營勞動,太平軍的樅陽會議、共產黨的廬山會議體現的就是索要經營勞動。亞當·斯密將生產經營勞動的提供者即司商家,視為「非生產勞動者」,因為他們的勞動時數「不能保藏起來,備日後雇傭等量勞動之用。」作者認為:其一,斯氏將生產經營勞動視為非屬生產勞動乃屬錯誤。今天看來,斯氏所說「非生產勞動者」應為「非生產作業勞動者」之誤。其二,斯氏認為所有司商家無一例外地是「非勞動者」,因此如下公式「不勞動者不得食≠資本家是吸血鬼」,應是斯氏心中公理樣式看法。作者馬上就會談到生產作業勞動和生產經營勞動的分別,以及兩者與交換價值的關係。
馬氏曾經說過,物質生產、精神生產、人類物種的自我生產、社會關係的「重新生產」(亦可稱為「複製」——作者注)這四種生產形式,始終存在於歷史之中,因而是人類生產的普遍形式。在此,馬氏混淆了生產勞動和索要勞動:部分「精神生產勞動」應屬精神索要勞動;「人類物種的自我生產」和「社會關係的重新生產」,應屬人類物種的自我索要和社會關係的重新索要;「物質生產」則應祛除「物質佔有」。
顯然,追求生存、安全、順悅屬於人類物種的自我索要;追求權力、地位、名望屬於社會關係的重新索要;追求知識則既屬於對於天–人關係之中客觀規律的索要(自然科學),又屬於對於社會關係之中客觀規律的索要(社會科學),而且都是逐步升級的索要。「自我生產」中的「自我」,「重新生產」中的「重新」皆可暗示:馬氏曾下意識覺察到,人類物種和社會關係都屬於天設效用——「自我」意味著自在,「重新」涉及到母型,遺憾的是,唯生產力論即經濟仲介決定論,阻礙了馬氏從勞動一次劃分論者變為勞動二次劃分論者。
附帶說明,由此觀之,鄧小平的「科技人員也是勞動者」的論斷乃有實證根據,並非只是定心丹丸——這兒的「勞動者」,便是索要勞動者。
美國學者哈·拉斯韋爾將使用價值——又稱效用——破天荒地分為八類,即:壽康、財富、技能、啟蒙、權力、尊重、正直、情誼。這一分類對於作者此次成功證非馬學的巨大作用,怎麼強調都不過分!不過作者認為,「情誼」應當擴大內涵與外延,換成「順悅」——順覺、愉悅的合稱,突破僅涉愛情、友誼之限。「春風得意馬蹄疾」,不也是古代中國十萬進士所追求的嗎?不僅是「紅袖添香夜讀書」吧?普通話、廣州話以及各地方言,熟人相見,都有「近來怎樣,順還是不順?」一問。
財富即是令人囊藏增值的實物收入和勞務收入。不過,天設財富和其他七種效用都是天設效用。從種類上說,天設效用與人造效用之比為7.5:0.5, 即為100:007, 十種效用當中只有零點七種效用屬於人造效用。忽視或者無視涉及天設效用的交換的經濟科學,顯然是揀了芝麻丟了西瓜,但這不幸正是當代西方主流經濟科學和中國官方經濟學說的現狀。
以下作者結合拉斯韋爾本意,針對七種純粹天設效用再作一番本人有所發揮的解釋:
壽康乃指生存和安全(包含健康)。技能可使任何實踐——如藝術、手藝、貿易、科學、教育、文化、衛生、傳媒等的活動——變為熟練。啟蒙涉及資訊、見解、知識、發現等。權力本是政治科學的中心概念,即「A若能達到令B去做其原來B無意去做之事的地步,A便可稱對於B擁有權力」——後面還會回到美國學者羅·達爾的這個操作性定義。領受尊重的載體,包含地位、榮譽、承認、威望、榮光、名望等。正直乃一倫理價值,應含美德、善心、忠直、信用等。
生存、安全先於意識、勞動甚至進化、語言出現,自是不必多說。技能可被掌握,知識可被發現,甚至假造,但亦非人力所能製造。權力、地位、名望、正直均屬社會關係效用,都與「意欲支配別人」有關——亞里斯多德嘗言「人類乃是天生政治動物」。誠哉其言!人類只能在戲劇之中仿生製造權力、地位、名望、正直。人類的順悅,如快感——飽快感、性快感、成快感、知快感等等、愛感和美感,滿意、隨意和得意,可被人造效用喚起,亦非人力所能製造。若無回應基因,人類便會呆若木雞。人類追求喜樂卻不追求怒哀:荷蘭科學家們的一項研究表明,人類天生就會笑,而哭是後天學會的。也許有人會說,順悅、名望並不重要,可予刪除。其實不然,英國一項民意調查表明:如果生命只剩兩個小時,大多數被詢者都會選擇與心愛之人互訴衷腸,相擁相吻或者上床做愛,從事靈肉交流而非其他活動,包括為國捐軀之類。而亞當·斯密說得分明:「名譽的尊卑一端,對於一切體面職業,可以說是報酬的大部。」現今不是流行「人氣=財氣」的公式嗎?
上述八種效用盡可進行類內交換,馬氏就曾說過,人與人之間「只能用愛來交換愛,只能用信任來交換信任,等等」。類際交換對於八種效用來說亦為全然適用。例如:
自殺爆炸:壽康與財富的交換;
高薪聘請:財富與技能的交換;
體腦相長:技能與啟蒙的交換;
筆劍互衛:啟蒙與權力的交換:
洋人朝廷:權力與尊重的交換;
貞節牌坊:尊重與正直的交換;
冰海沉船:正直與順悅的交換;
英雄救美:順悅與壽康的交換。
權錢交易:權力與財富的交換;
官包二奶:權力與順悅的交換;
財色交易:財富與順悅的交換;
納粟拜爵:財富與尊重的交換;
開館授徒:啟蒙與財富的交換;
為帝王師:啟蒙與尊重的交換;
好人平安:正直與壽康的交換;
以德服人:正直與尊重的交換。
不恥下問:尊重與啟蒙的交換;
危地探險:啟蒙與壽康的交換。
類內交換亦然可與類際交換交叉,並行不悖。例如,紅軍長征期間,劉伯承將軍與小葉丹頭人之間的槍支(財富與權力)與通道(生存與安全)的交換,同時也是信任與信任的交換——在此乃以歃血為盟公開表達。政治結拜在此代表安全,就像商業信用通常代表安全一樣。而對於當代中國普遍百姓來說,權錢交易,財色交易乃是他們見慣不怪的交叉交換——受賄貪官與行賄刁民之間同時交換著信任;好色富商與緋聞女星之間同時交換著名望。
顯而易見,索品交換——又可稱「社會交換」——的歷史、規模、頻率、變化,必然遠遠超過產品交換——又可稱「經濟交換」,儘管總量未必。社會交換和經濟交換的交叉簡稱「社經交換」,還原的話,簡稱「索產交換」。除了交換之外,人類還有贈予、遺傳、遺失、分配等讓渡形式。在此必須馬上聲明,在作者眼中,「分配」必然涉及威權:有被分者就有施分者,因此「按勞分配」之中的「分配」實為交換,「按需分配」之中的「分配」才屬分配;下面將會談到「按勞分配」應當改稱「按效交換」或者「各取所值」。將「分配」與「交換」和「配置」區別開來,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以往的混用已使人們吃盡苦頭。交換的原則是平等,分配的原則是差等。顯而易見,交換活動只有「交換雙方」,但卻既沒有「施換者」也沒有「被換者」,人們僅於語義學的角度,便可覺察得到經濟學與政治學的分野。馬克思錯誤地將人類經濟活動分解為生產、消費、分配、交換四種,乃是因為沒有與時俱進或者抽象不夠。封建主義社會「君賜」無所不在,「封」即是威權分配;資本主義社會「商取」占了上風,「資」乃為交換所得。
毫無疑問,產品及相關勞務,索品及相關勞務,均可成為商品,只要其被用於交換。
如果商品交換的依據,乃是最後以馬氏所說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基準的「勞動時數」的話,那麼,一切產品及相關勞務,一切索品及相關勞務,其收凝的或者流淌的勞動時數,就必須是普遍地,恒常地可被間接測量(下文馬上談到何謂間接測量)通約的,即使此種時數乃為變動不居,亦須如此。這是不言而喻的,某項商品的收凝勞動時數如不可被測量通約,則其交換價值便必不可被確定,如果世間的交換價值乃以勞動時數充當依據的話。讀者稍作琢磨即知:在《證非二十義》中,已無必要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個別隨機勞動時間」作出區別對待。
但是,顯而易見,只有在相對其他三種勞動形式而言,場地和工具固定,人員和角色明晰,供產和流銷重複,產品和勞務分明的生產作業勞動之中,勞動時數才是可被被普遍地,恒常地間接測量通約的;而在沒有或者缺乏類似條件的生產經營勞動,索要經營勞動、索要作業勞動之中,勞動時數則是難以乃至無從被間接測量通約的。
配第、布阿吉爾貝爾、坎蒂隆、斯密、李嘉圖、馬克思(以下簡稱「配、布、坎、斯、李、馬」)等人的勞動價值學說,不論是一元論的還是多元論的,以及當代西方主流經濟科學,當代中國官方經濟學說,全部都沒認真考慮這種「一明三盲」的現象,從而生成人類認知歷史之上的最大的一個「黑洞」,人類實踐歷史之上最大一個錯誤——兩者都是最大,不是最大之一!當然有人會說,沒有測量並不等於勞動價值沒有凝固其中,作者對此不持異議。作者想說的是,既然沒有或者無從間接測量勞動時數,交換之時何能以勞動時數作根據?
作者若是沒有學過公差測量、經濟統計、概率初階、高等數學,僅靠美國行為主義學派給予的訓練背景,斷難捕捉得到此一現象。
生產經營勞動和生產作業勞動乃是一對孿生兄弟,「勁往一處使,汗往一處流」,鵠的皆為人造效用。但是即使如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那刻意與馬學奠基「公理」保持一致的「社會主義統計學」,也不無遺憾地聲明:不能將經營勞動的成本平攤到作業勞動的成本——即為直接費用亦即合格產品的成本之中去,因為這樣做了,便會「歪曲產品成本」,令環比、同比失去信度。眾所周知,生產企業時常都會發生經營時數(人均工作時數×人數)雖大幅增加,產品數量卻大幅下降的事情,反之亦反是;或者時常發生產品數量雖有升降揚抑,經營成本卻為巋然不動的事情;經營時數增加——例如冗員過多,生產企業反而破產的事情亦非少見。顯而易見,「生產經營勞動」與「人造效用產出」僅呈因與果正相關,不呈量與量正相關。此謂:生產經營勞動「時不函價」。如前所述,亞當·斯密曾說,生產經營勞動時數「不能保藏起來,備日後雇傭等量勞動之用」。勞務或曰服務勞動何嘗不是這樣?
而在索要作業勞動(如中越界山保衛戰)和索要經營勞動(如劉備孔明隆中對)之中,由於受到諸多想像得到的或軟或硬的條件限制,由於植入人體計時晶片之事迄今尚未普遍發生,勞動時數則是更加難以乃至無從被普遍地,恒常地間接測量通約的。即使個別地、偶然地可被或者易被間接測量通約,一旦時間長度成為要素,人們就會發現:索要作業勞動時數,索要經營勞動時數的升降,與合格索品數量的升降,僅呈因與果正相關,不呈量與量正相關。索要勞動時數換取不到索要勞動成果的事情,更屬常見,譬如,什麼叫「你死我活」、「誓不兩立」?另外,讀者不妨掩卷思之:趙匡胤陳橋黃袍加身,歷時多久?李自成出陝入主北京,耗年幾何?結局異同?享祚長短?
由此可知,出於「條件並不許可」這條極為明顯的理由,人類自古以來便從無起念測量通約索品,及相關勞務收凝或者流淌的勞動時數,以便開展與產品及相關勞務的交換,從來沒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即使有人想過測量,似乎也不可能在個、共兩相方面加以測量,這不是理論本身有何缺陷,而是索要勞動的不確定性就像量子世界的不確定性一樣,必然會帶出「測不准原理」。
由此不難推出:人類若選擇勞動時數作交換依據,則商品交換的絕大部分個案,勢將無法進行,原因不言自明:若間接測量通約不能行,則勞動工時資料不能全。從理論上說,前文所列十種商品交換,只有第一種、第四種、第六種這三種可以接受間接測量通約,其餘七種皆不可以接受間接測量通約,由此可以推知,商品交換的依據絕無可能鎖定勞動時數。
下舉一則顯例,繼續說明上理:
以權力、地位交換糧食、貨幣的中國歷代王朝的「賣官鬻爵」制度,由秦及清,持續長達二千年之久。此一制度,輔之以「五均六筦」制度和「以德代道」文化,對於中國的官本主義社會的形成,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古代官本主義社會,曾經盛行以官名冠平民這種舉世罕見的風俗。例如,稱讀書人為「相公」,有錢人為「員外」,典當商為「朝奉」,醫藥士為「大夫」,工匠頭為「待詔」,官子弟為「衙內」,行婚男為「新郎官」、茶侍應為「茶博士」……此種風俗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古代中國社會乃為「官入膏肓」。「以官為本」不僅僅反映在「以官為榮」、「十民九牧」、「官刁勝民」之上,而且反映在「權錢交易」、「權糧交易」、「權色交易」之上。一位親中國菲律賓女議員曾因快人快語道破「中國創造了貪污文化」,而受到中國政府的抗議。如果稍變說詞,將上語改成「中國具有世上首屈一指的權錢交易、權糧交易、權色交易的傳統」,倒是可謂一語中的。讀者不難看出,賣官鬻爵的三個具體形式,即上述三種交易,其交換依據完全沒有可能歸於勞動時數:交易雙方曾有何人何時何處間接測量、通約、表達、談判過收凝於用以交換「國授權力」或者「國頒地位」之中的勞動時數?
商品交換的依據,迄今只有已為當代西方微觀經濟科學約略點出的「效用序數」一種可資候選。依照作者之見,單位基準效用序數只可能是「勻質效用序數」,不可能是龐巴維克曾作妄斷的「邊際效用」,本書第17章將會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前述之權威的約·布萊克編之《牛津經濟學詞典》,關於「勻質效用價值說」並無專設詞條,可見該說在西方學術當中還未引起注意,已被邊際效用價值說擠兌得不成樣子。
源于表現人類心理對於有所需求的索品及相關勞務,或者產品及相關勞務的社會屬性或者理化屬性的滿足程度的「效用序數」,乃是時時處處都可成為商品交換的依據。中國先哲程頤曾經斷定:「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由此看來,上述「滿足程度」便是可以「人同此心」,而非「異人異心」的。源於「抽象滿足」而非「具體滿足」——這裡是在模仿馬氏的「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的效用序數,訴諸的是人腦之內的感知機制,而非人腦之外的測量尺具。此種感知機制乃屬於全人類的「類本質」。腦在,則作為交換資料的效用序數必定可得,主觀客觀熔於一爐;尺在,則作為交換資料的勞動時數未必可得,主觀客觀從中斷裂。以類型學角度觀之,效用序數的可得性已然是百分之百,勞動時數的可得性則只是百分之七而已。人類完全沒有可能放棄效度高達百分之百的依據,轉取效度僅為百分之七的依據。當市場供求平衡之時,價格反映的是未受供求變動影響的「社會靜適效用序數」,可稱「出清價格」。與主由供方決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同,「社會靜適效用序數」主由需方決定。
誠然,序數遠遠不如基數精確。但是在賣方心理、買方心理、貨幣實值三者均在時時變動的情況下,貨幣反映價值的精確又有多少意義?久而久之,人類對於精確交換的要求勢必趨於減弱,對於模糊交換的認受勢必趨於增強,「大概齊」勢必驅逐「算死草」,序數勢必驅逐基數。世界首富之一巴菲特說得再好不過了:「我寧願要模糊的正確,也不願要精確的錯誤。」月票制、年票制、會員制、合作制等等,就是一類典型的雖然不喜歡錙銖必較,但卻可致皆大歡喜的模糊的商品交換方式,換成精確的商品交換方式,反而會令交換雙方感到不便。
由上多重論述,可以得出結論:源於配、布、坎、斯、李五氏,峰于馬氏的勞動價值學說,可謂萬古糊塗之論,誤盡世人之說。史達林、毛澤東時代的國有企業,計劃經濟帶來生產供給恒萎,社會亂象頻生一事,業已雄辯說明:鎖定勞動時數為交換依據,既然有悖自然法則,必會招惹天譴。至此,共產國家億兆人民方才明白,不應光是譴責斯毛二氏,還應追溯譴責配、布、坎、斯、李、馬六氏——不是總說「行動從思想來」麼?
必須指出,人類從事商品交換之時,絕無可能使用多於一種的交換依據。例如,混合使用「產品交換依據」、「索品交換依據」、「產索交換依據」之類,百花齊放;同時絕無可能在不同的交換依據之間來回切換,這就像人類無絕可能一族飲水,一族飲烷,一族飲汞一樣。反過來說就是,經濟交換必須使用與社會交換,經社交換完全一致的交換依據;各種交換內部,也必須使用與類際交換一致的交換依據。造化教會人類形式邏輯,豈容交換中的同一律橫遭破壞?然而,正是馬氏本人在他篤信勞動價值由淺入深之前,概念混亂地說過:「在沒有階級對抗和沒有階級的未來社會中,用途大小就不會再由生產所必要的時間的最低額來確定,相反,花費在某種物品生產上的時間將由這種物品的社會效用大小來確定。」馬氏歸根結柢竟是效用價值論者!且不說恩氏曾經說過「價值是生產成本對於效用的關係」了。試問:人類大腦灰質有沒可能存在兩種不同的的價值評定機制?人類雌雄個體有沒可能存在兩種不同的生兒育女機制?
作者相信大腦神經科學今後的發展,必定會為此處主張的命題提供更多更好的實證。在大腦灰質與效用價值之間許有「量子糾纏」。
簡而言之,若視勞動時數為價值本數(LV = Labour Value)——價值末數乃為受到供求波動影響的市場價格(MP = Market Price),則此種價值本數只是一種謊量(謊花的謊)或曰岐量(AV = Ambiguous Value)而非信量。勻質效用序數(UUV = Uniform Utility Value)則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如假包換的,世間唯一的價值本數。就像植物花朵既有又開花又結果的,亦有只開花不結果的一樣,勞動時數也既有測時可果的,亦有測時不果的,因此泛泛而談勞動時數,不管是「社會必要勞動時數」還是「個別隨機勞動時數」,只能落入謊量或曰岐量之列。只能如此,豈有它哉?
前人所說「絕對效用」乃指「商品滿足人類需要具體屬性」;「相對效用」乃指「商品適應市場需要程度」。據此,作者還做一種猜測:抽象效用序數可能就是相對效用序數,亦即商品可得難易程度,此種難易程度乃由四個向度混成:自然資源可得難易程度、四種資本籌集難易程度、製造過程勞動難易程度、產品研發技術難易程度。
出獄以後,作者方才看到國內學者:其一,湖南師範大學教授羅朝暉所作的一種自人類探討如何計算價值以來異峰突起的,關於商品如何定價的天才猜測。他的的解釋乃與作者香港經商所得經驗並無二致。自然科學中亦常見使用這種「因為結果近似不妨以簡法代煩法」:
那麼,現實當中,生產者或消費者是怎樣擺脫勞動價值論者和效用價值論者(因難以計算商品價值而引起的他們——作者注)的煩惱的呢?應該說辦法並不複雜,就是利用了市場的競爭機制,加上稍微精確的成本核算。一種新產品上市,它的定價不外乎兩種情況:一種是高於成本價,一種是等於成本價。如果是第二種情況,就不會有競爭廠家加入;如果是第一種情況,因為有超額利潤,馬上就有競爭廠家加入,知道商品賣價與成本價不相上下。消費者則是參照商品的價格、效用情況及自己的購買力來確定購買數量的,他們的購買數即是供給者的供給數,供給者如果是按照這一數量去生產,則市場上這種產品供求平衡,此時的價格即均衡價格,也即產品的價值。當然,這裡面的競爭應該是完全競爭或接近于完全競爭。因而,只要排除了壟斷,產品的價值事實上是無需使用價值理論來進行精確計算的。
其二,曹國奇曾以經濟學家的嗅覺辨識出「按資分配」、「按效分配」、「權力分配」、「名譽分配」、「救濟分配」、「教育分配」,以及「政治和外交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涉及分配標準,以決定各要素、各部門、各國家分得價值(或利益)多少」,其三,鄭根權已經認識到了,由於社會是經濟、政治、文化的綜合體,所以相應地剝削有著三種形式,即經濟剝削、政治剝削或稱權力剝削、文化剝削。政治剝削和文化剝削有著自身的運行方式和規律。讀者可從曹鄭二氏論述當中,看出本書引述的拉斯韋爾的八大效用分類、伊斯頓的政治定義的影子,說明國內學界大有思想開放兼且明敏之士。不過,可惜的是,曹氏沒有想到;「過去無人測量權力、名譽勞動時數,權錢權色交易、人氣財氣轉換也可實現」這一要害問題。鄭氏未能從「剝削乃為源自持續的不平等交換」這一點,進一步悟出「人造效用與天設效用交換、天設效用與天設效用交換必不可能以勞動時數為根據」。
第一章的核心概念,可以濃縮成為六字:索品無法測鐘。
如前所述,在廣州話裡面,「鐘」指時間,此處和以下引申為「決定交換價值的勞動時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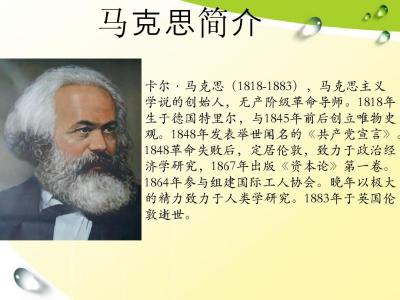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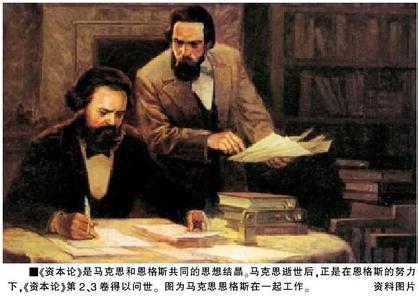

美國學者哈· 拉斯韋爾

美國學者大衛·伊斯頓

中國學者鄭克中顛覆馬學元論巨著
